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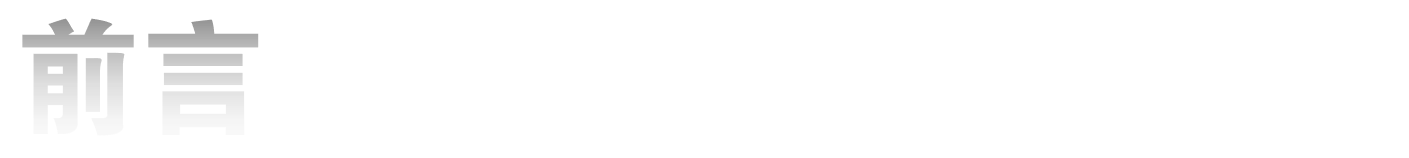
文明是人类的独特创造,它既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又是人的自由选择。
文明和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和文化科学的重要问题。
本文共计2821字
阅读时长约5min



文明与文化科学的区别
哲学是研究文明体系内的人性质素,那么,文明和自然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也是文化科学的问题,但是,哲学和文化科学的角度不同。
文化科学认为文明是一个自主的领域,然后探讨文明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目的是描述文明的结构和规律。
哲学则要说明文明怎么能成为一个自主的领域,文明和自然的区别在哪里。

人的起源和性质
文明是人的生存方式。
这句话意味着:
人的生存方式不是自然的一种形式。
文明意味着超越自然,包含着自然没有的新的东西。
对文明之超越自然的性质进行考察,就是哲学的领域。
文明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其实是人的起源和性质的问题,因为文明是人的生存方式。
有文明创造力的存在物,表明他和其他存在物不一样。
对这种不一样的地方的研究和解释,构成人学问题。
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种起源的学说也用于解释人的起源。
这种解释以科学的原则参与了反对宗教和神学的运动。
人不是上帝造的。
人来自动物,特别是来自类人猿。
人和类人猿在生物上有联系。
类人猿是人的祖先。
人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是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
这种进化论的人之起源说被普遍接受。
按这种说法,人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生物。
这种说法以科学的原则强调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一致性,在人的问题上彻底贯彻了自然主义。
但是,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进化学说,还有一个基本难题:
人之作为生物的自然起源,不能直接说明人之作为有文明创造力的存在物的起源。
人是最高级的灵长类动物,但这里的“最高级”,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的,这种角度,只是把人的智能看成是自然的最高级的形式。
但是,人的智能本身不等于文明的创造力。
如果把人类幼体和社会世界隔离,他即使长大了,他的天生智能也不会超过聪明的类人猿。
所以,当谈到文明起源问题时,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解释原则就不适用了。
而且,不仅不适用,甚至要求对达尔文的单纯进化的原理进行修正。

人的未完成性和尝试学习的能力
有意义的观察表明:人和动物的相似,主要是人和幼年类人猿的相似。
幼年类人猿比成年类人猿更像人:
幼年类人猿的头骨、四肢和毛发和人很接近,它们的心智也比成年类人猿更有好奇心、更有学习的能力。
这种类人猿幼体,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是未完成的类型,是灵长类的原始类型,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阶段,类人猿只有在幼年时才有这种特征。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发:
人不是从成熟的类人猿进化来的,相反,人没有完成自然要求的进化,而是停留在一个未成型的过渡阶段,类人猿才真正超过了过渡阶段而进化了。
从生物学的原则看,相比人,类人猿才是更进化了的物种。
这样说的依据,是生物进化论原则本身。进化论原则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就是物种的器官要适应它们的生活环境,这就是器官的专门化。
器官的适应能力,构成动物的本能,而本能则决定了动物的行为。
所以,高度专门化的器官和适应能力,是物种完善性的标志。
比如,老鹰的眼睛、爪子和胃,使它成为典型的食肉类猛禽。
与动物相比,人的器官没有达到高度的专门化,相应地,人在本能上也很贫乏。
比如,人的牙齿既不是专吃植物的,也不是专吃肉类的,所以,自然没有规定人是什么食物;
再比如,人的生育没有季节的限制,人的性活动也没有特定的时期。
这些都表明,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在本能上是不完善的。
作为一个物种,人有未完成性。自然好像只造了人的一半,就让人自己去完成另一半。
在这一点上,人就已经和其他自然的动物不同了。
他要么因为器官的非专门化和本能的贫乏而被自然淘汰,要么靠自己形成一种生产和创造的能力去适应自然而生存。
这种生产和创造,不是人改变自己的生物本性(这是自然的事),而是人根据自然条件去形成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文化,就是文明的创造活动。
所以,人要么作为一个怪种而灭绝,要么保持和发展幼年类人猿的尝试和学习的能力,并把尝试和学习看作是自己永远的任务。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文明和自然的契合点。
自然给一个物种留下了不完善性,也给了它尝试和学习的潜能,并用生存的压力迫使它通过发展尝试和学习的能力去形成一种超越自然本能的生存方式。
这样,非专门化和本能的缺陷,就变成了有利的因素。
也正是在文明和自然的这一契合点上,我们看到了文明之区别于自然的根据。
文明作为人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适应自然的创造活动,是在本能贫乏的基础上,达到生产的自我决定的自由。
所以人不仅要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要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世界中。

人的生存方式
文明的创造,作为一种必然性,根植于人的存在结构中。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被罚为自由的。
动物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它不能超越自然给它的形式,也不能低于这种形式。
但自然没有给人任何确定的生活形式,人必须在自己的文明创造中寻求确定的生活形式。
这就是人的自由的出发点,也是文明起源的必然性。
如果我们问:
有什么样的存在物,既是被造的,又是造物者?
或者说,它靠什么来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规定?
这是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上面的讨论,是从自然的科学原理出发,揭示了文明起源的外在必然性(这一必然性表明:没有文明,人这一不完善的物种必定被淘汰),但我们还没有揭示文明之必然形成的内在根据。
文明就是人的文化世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人必须生活在自然界中,但人只有通过生活在文化世界中,才能真正生活在自然界中。
我们已经说明,文明不是自然的一种形式,不是自然力的最高级的形式。
但是,对于人的思维和意识而言,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却是一个不自觉的自发过程。
人必须自由,才能创造文明,但这个创造过程又不是自由自觉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这个悖论构成了人之谜。
人之谜,也就是文明之谜,历史之谜。
文明的创造,对于自然的盲目必然性而言,是自由的,但对于人的理想能力而言,是必然的。
用一个象征的说法,人会这样说:我做了自然没教我做的事,但我也没预先设计好这件事,就像我在自然的荒漠上开辟了一条路,但我却感到是被一种我不知道的力量推着走,我对这条路和它的目的地感到惊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类的社会世界还属于必然王国的领域。
马克思这样写道:
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但人又是人的奴隶,是他自己的卑贱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粹之光,似乎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的背景前面生辉。
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的成果,似乎仅仅赋予精神的生命以物质的力量,而抽掉了人的生存,使之贬低成一种物质的力量。
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的人的生存,不是一种物质的活动,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包含人性的精神质素。
如果把人性的精神质素贬低成一种物质的力量,这就是精神的力量被自然必然性所取代,或者说精神的力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但是哲学不仅要揭示这一点,更要说明这一点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说明要从文明之必然形成的内在根据开始,然后用这个根据去认识人类精神之自觉的艰难道路。



